《大明高僧传》,简称《明高僧传》,八卷(清藏作六卷),明代释如惺撰。如惺号幻为,为天台宗真清的弟子,复从千松得禅师习禅宗,曾住天台山慈云寺及嘉兴楞严寺,除本传外,还有《得遇龙华修证忏仪》四卷,今存(见袁黄撰《象先禅师塔铭》及管志道撰《龙华忏仪序》)。
此传作者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自序中谈到前代高僧传止于宋初,以后无人续编。同年,又将在庚子岁 (1600)校刊的《金汤编》加以补辑。作者在涉猎史志文集中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随喜录出,从南宋到明末共得若干人,题名《大明高僧传》,以备后来修史者的采摭。书名“大明”乃指编撰的时代而言,不是指的内容范围。他本拟上继《宋高僧传》,但《宋高僧传》止于北宋初,此传则始于北宋末,中间相隔一百数十年,仍有一段空白。
此传只有《译经》、《解义》、《习禅》三科。《译经》科中著录的仅元代沙啰巴一人,《解义》科中著录的自南宋迄明万历间四十四人,《习禅》科著录的自北宋末迄元仁宗间六十七人,共正传一百一十二人,另附见六十八人。其中普交卒于宣和六年(1124),则是北宋人,序中所言始于南宋,当是作者的忽略。又《习禅》科没有著录明代僧人,也无梁、唐、宋僧传的后面七科,可见是尚未完成的著作。传中著录的僧人,大都居南方,居北方者仅数人,金僧仅教亨(卷五)、海慧(卷七)二人。
此传根据的史料,作者没有指明。但可以考知的,如必才、允若(卷一)、弘济(卷二)、士璋、大同、慧日(卷三)诸传,是据宋濂撰的《大用才公行业碑》、《若公塔铭》、《天岸济公塔铭》、《璋公圆塚碑铭》、《别峰同公塔铭》、《东溟日公碑铭》(均见《宋学士文集》卷五、五十二、五十七、五十八、六十)等而成。真清的传(卷四)是据袁黄撰的《象先禅师塔铭》(见《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四)而成。《道震传》是参考晓莹的《罗湖野录》卷上而成。全书《习禅》科绝大部分是据《五灯会元》删节成篇,因而语录的气氛很浓厚。又教亨(卷五)、崇岳、道悟(卷八)等传皆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沙啰巴(卷一)、文才、英辩、德谦、达益巴、妙文、了性、宝严(卷二)等传皆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写成。至《沙啰巴传》中所说:“今于《元史》仅得此人”,史字当是世字之误,因《元史》中不载沙啰巴,而在《元史·释老传》卷二百零二中则有必兰纳识里的传,必兰纳识里曾译经六部,不为本传所载,足证作者没有利用《元史》。
此传体裁与以前的梁、唐,宋三部僧传同,而每科之后无“论”,当是因为全书尚未完成之故。有的传后有“系曰”,则是仿自《宋高僧传》。在“系曰”中,透露出作者一部分观点。《祖觉传》(卷六)“系曰”:“古为人师者……,未尝轻许而贼夫人子;今人才见灵利后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顿焉称赏。”《弥光传》(卷六)“系曰”:“世之灵利汉,靡不坐晦庵(弥光)膏肓之疾……曾未服医父起死回生之剂,且急欲为人指迷,不亦谬乎?”《蕴能传》(卷七)“系曰”:“世之师徒宾主相见,能具此(大沩瑃禅师和蕴能)风采作略,庶两无遗憾”。明代末叶,禅宗极盛而混杂,师徒之间,问答之际,颇多狂禅滥调,自谓解人。作者此论,当是针对时弊而发。《法忠传》(见卷五)和《自回传》(见卷六)的“系曰”都指出习教者固执门庭,歧视禅家,不知禅宗自有悟处,则是调和禅与教的论调。各宗融和,正是时代要求的反映。
此传在编纂方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首先,一些篇传所载事迹较略,如性澄、蒙润(卷一)、本无(卷二)、祖儞、如玘、绍宗(卷三)在《续佛祖统纪》中都有传;又了然、若讷(卷一)在《释门正统》(卷七)中有传;善悟、士珪(卷五)在《僧宝正续传》(卷四、卷六)中也有传,所记事迹和卒年等,都较此传为详,可以参阅。另外,在个别地方也时有错误:一、祖觉在卷一有传,卷六中又重出,而卷六的传系据《五灯会元》,较卷一的传为详,未将二传合并,误作二人,分入二科,实嫌疏忽。二、沙啰巴姓积宁氏(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允若俗姓相里(见《宋学士文集》卷五),乃认积宁、相里为地名、误作籍贯。三、又《文才传》谓元成宗署才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祐国住持事”。按《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洛阳白马寺是佛教创始的庙宇,故称“释源”。其宗主殁,诏以师继之。作者删节不当,乃致原意晦碍难明。四、此外,《宗杲传》作绍兴三十一年(1161)卒,应据《大慧年谱》作隆兴元年(1163)卒;《道冲传》作理宗三年(原书年号不明)卒,应依赵若琚撰的《径山痴绝禅师行状》(见《痴绝道冲禅师语录》卷下)作淳祐十年 (1250)卒为确。五、建文帝出家号应能事,为千古疑案,传说纷纭,殊不足据。作者谓《应能传》“于僧传是不可阙”,实则阑入不可靠的记载,有欠妥当。
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是随喜录之,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因而没有严肃加工整理,不免存在缺点,尤其不是全豹,不能算作代表某一时期的综合传记,也无法满足后世的要求。虽然如此,但是在本书中还保存了一部分为它书所无的传记,而且纂集三个朝代部分僧传在一起,对佛教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过去这类传记缺乏的年代里,将它作为前三部高僧传的继续,实际它是很难和前三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僧传相并提的。
(苏晋仁)
佛教词典 > 中国佛教 > 正文
《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唐代善导(613~681)撰。本疏简称《观经疏》,内分玄义、序分义、定善义、散善义四部分。所...凡十四卷。宋代从义撰。又作天台三大部补注、三大部补注、大部补注。收于卍续藏第四十三、四十四册。本书补注智顗之...(杂名)又曰绀发。佛顶上之毛发,为绀青之色也。大般若三百八十一曰:世尊首发修长,绀青稠密不白。...(地名)外道以竹杖量佛之身量处。西域记九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东行三十余里,至泄瑟知林,唐言杖林。竹竹修劲,...【九十八随眠中缘有漏缘无漏分别】 p0098 俱舍论十九卷十三页云:九十八随眠中,几缘有漏?几缘无漏?颂曰:见灭道...(术语)法华经所说十如是之一。报者应报也,下自地狱界,上至佛界,各如法依于过去善恶之业因而得今生苦乐之报,依...亦名:布萨时节、三日说戒、说戒日通三 子题:不得晨起布萨、布萨日通含三日、说戒克取十五日为定、净心说戒、三日...(术语)香,总嗅于鼻者。为十二入之一,故云香入。...【谛顺忍定】 p1377 无性释六卷十五页云:复由四种如实遍智者:谓如先说于名事等不可得中,已得决定。如是转时,悟...谓于菩萨四加行位(四善根)中暖位所得之禅定。此禅定为初步定慧之阶段,能观察对境之名、义、自性、差别等四法皆自...【于相善巧四种功德】 p0752 瑜伽十九卷十五页云:谓如有一,有学见迹,能善了知止举舍相。由此因缘,得四功德...八大人觉经...闻如是:一时佛在拘夷那竭国如来三月当般涅槃与诸比丘及诸菩萨。 无央数众来诣佛所,稽首于地。世尊寂静默无所说,光...(印光大师校印本)... 实际我个人24岁出家到现在60岁,我们师父们也可以见证,我每天虽然累,但却很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我选择了...年底的时候,是游子归家的时候,更是父母期盼的时候。 如果你,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回家的成本太高等原因,而不想...
实际我个人24岁出家到现在60岁,我们师父们也可以见证,我每天虽然累,但却很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我选择了...年底的时候,是游子归家的时候,更是父母期盼的时候。 如果你,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回家的成本太高等原因,而不想... 二佛神咒里面有勤转念,证菩提这两句话。虽然只是短短的六个字,但已经把修行的方法都告诉我们了。 我们知道,在我...
二佛神咒里面有勤转念,证菩提这两句话。虽然只是短短的六个字,但已经把修行的方法都告诉我们了。 我们知道,在我... 【原文】 阿弥陀佛慈悲愿力,遍周法界,普接众生,作大摄受,不令漏失。阿弥陀佛阴入界①身,遍同法界,普示众生,...
【原文】 阿弥陀佛慈悲愿力,遍周法界,普接众生,作大摄受,不令漏失。阿弥陀佛阴入界①身,遍同法界,普示众生,... 修行人要求一生事办,疾出生死,只有念佛法门。因为念佛一方面是仗自己的信力、愿力、净行之力。另一方面更加有阿弥...一青年向一禅师求教。 大师,有人赞我是天才,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也有人骂我是笨蛋,一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依您看...
修行人要求一生事办,疾出生死,只有念佛法门。因为念佛一方面是仗自己的信力、愿力、净行之力。另一方面更加有阿弥...一青年向一禅师求教。 大师,有人赞我是天才,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也有人骂我是笨蛋,一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依您看... 宝通禅师初参石头希迁禅师时,石头禅师问道: 哪里个是你的心? 宝通回答道:见语言者是! 石头禅师不以为然地说道...
宝通禅师初参石头希迁禅师时,石头禅师问道: 哪里个是你的心? 宝通回答道:见语言者是! 石头禅师不以为然地说道... 印光大师的十念计数法是把慈云尊者的十声念佛,就是呼吸念佛和数息观,这两个把它整合起来,运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
印光大师的十念计数法是把慈云尊者的十声念佛,就是呼吸念佛和数息观,这两个把它整合起来,运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
大明高僧传
【中国佛教】
| 上篇:宋高僧传 | 下篇:比丘尼传 |
(692~771)唐代僧。山阴人,俗姓张。景龙年间出家,精通内外之学。初从昙胜学行事钞,后游长安,师事相部宗太亮,...
观无量寿佛经疏
法华三大部补注
绀顶
杖林
九十八随眠中缘有漏缘无漏分别
如是报
说戒时节
香入
谛顺忍定
明得定
于相善巧四种功德
【大藏经】【注音版】八大人觉经
【大藏经】佛说法灭尽经
【大藏经】【注音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一定要让学佛成为快乐的事
爱的细节

短短的六个字,把修行的方法都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怜念众生,生生世世不相舍离

能够这样念佛,一定可以了生脱死
一斤米的价值

什么是你的心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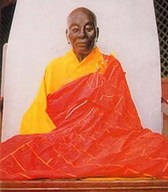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