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澍葊法师在清朝道光(公元1821——1850年)和咸丰(公元1851——1861年 )年间 ,在维扬(今江苏扬州)一带声名鹊起,法学远播,上到官府衙门,达官贺胄,下至茶肆酒楼,里苍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的。
但是,这位氏族、籍贯全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考证的澍葊法师,年少的时候为人却十分蛮悍、彪勇,横行乡里,欺压弱小;同时他又十分懒惰,游手好闲,无赖顽皮,所以,人们对他是恨之入骨,却又没法奈何。
后来,这位顽劣异常的子弟不知怎么一来就投身佛门、皈依三宝了。但是,他虽然身在佛门,而心思却一如尘俗之时,半点没有更改,放纵形迹,不持戒律。
就在他出家的扬州城里的一座寺庙里,有一回,他不顾清修净持,居然大摇大摆地来到厨房里,没等斋饭的时刻到来,就自顾一人地大吃大嚼起来。主管火厨的僧侣当然不允许他这样乱来,就好言好语地劝阻他。没想到他竟然无赖心性顿起,恶语相加,谩骂不止,甚至还想大打出手。正好有人偷偷地报告给寺中住持,住持赶到,才劝阻住他。
之后,住持便当着其他僧侣的面严厉地申斥、诃责了澍葊, 命他好生求学研习,不得惹是生非。如果还不知忏悔,一味行恶,就要将他驱逐出寺。
澍葊一听,心中忿懑异常,但当着这么多人面,却又不好顿时发作,但报复、泄忿之心,却在心中潜滋暗长起来。
到了晚止,他竟然又偷偷地摸到厨房之中,抄起一把十分锋利的菜刀,把它藏在僧房中自己的枕头之下,准备伺机图谋不轨,刺杀住持,然后逃之夭夭,浪迹江湖。
可是,夜深人静之后,澍葊躺在床上,看明月照窗,清辉四泻,却怎么也睡不着 —— 突然之间,他不免心生后悔之意,想:“我如果真的把住持几刀砍死了,自然,心中的怒气得以发泄,复仇之愿可了;但是,我这样做了之后,即便不论自己日后身浪天涯,可却怎么向神鬼、佛祖交代呢?”
就这样。善念一生。恶意顿消。澍葊和尚便决心努力修行,苦诵经律,以期修证正果。可是,他细一揣测,发现自己虽然皈依佛门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却几乎什么也没学会。心中不禁诚惶诚恐,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直到东方欲曙之时,他才突然想起住持曾经说过:“凭借一颗至诚之心,修持《大悲神咒》,也无不穷彻法源,妙证上果。现在,自己善念已生,虽然不会读其他经籍,但这《大悲神咒》还是会读诵的,为什么不修持这一律咒?
想通了这一层,等到天一亮,澍葊和尚便来朝参住持,先为昨日之事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负惭之意,以示忏悔。接着,他又请求住持,说自己愿意闭关三年,专持《大悲神咒》,希望住持能够不计前过,单给他开辟一间静室,以便悉心修持。
主持法师一听,不觉大喜过望,忙点头依允。
这样,澍葊和尚便来到寺中的藏经阁中,准备闭关修持。为了禁绝自己心有旁鹜,也为了提醒他人不要打扰自己的专心修持。他在正式入关之先,特地削了块木片,在上面大书“禁语”二字,悬挂在自己的胸前。偶尔,有别的僧侣登阁阅经,见澍葊想和他说话,澍葊总是指指胸前的竹牌,并不答理他人,只顾自己修行。
从此,不论寒暑,无论晨昏, 澍葊和尚总是一心修持,从不懈怠。等到春去秋来,三年飞逝,澍葊法师才出关,走下藏经阁。此时的澍葊法师,与三年前相比,人们却惊异地发现,他一改过去的悍勇、粗蛮之貌,神采奕奕,峻秀清空,真可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人们见了,无不对他尊敬有加,却又感到神异莫测,只是不知道他的佛法证得如何。
扬州一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即:无论文人学子,还是僧道门徒,无论达官显贵,还是下里巴人,无不喜欢盘桓茶肆,喊饮茶,或餐补,或小憩,或闲聊,无不适心自娱,进退从容。这种风习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成为当地时尚。
而当时,文人学子为了躲避清廷的文学狱,争相钻入考证的圈子中,致使有清一代,小学大盛。什么汤盘禹鼎,文物象数,士子们无不各夺一经,以求渊博,并一概称这制学问叫“汉学”。
当时,仪征(今江苏仪征县)人阮文达校勘《十三经》,普天之下,无不视他为宗师,执经叩问,以释疑难。而有的读书人无缘请益阮公,只好抱着厚厚的一大摞经籍文献,到这茶社酒肆中向人请教。
一天,几个读书人又在茶社之中就某一经籍文义互相诘难考问,争执不休。正好,澍葊法师就坐在他们的旁边,听他们你争我论,莫衷一是,不觉微笑起来,却没有开口说话。后来,这几个读书人终于发现身边的这位僧侣,品貌不凡,气质超尘,而他又自始至终只是微笑着倾听自己的争辩,并不多说一句话。他们心想:没准儿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僧呢!
大家这样想着,便一齐诚恳地向他请教。澍葊法师见状,就朗声答道:“你们刚才所谈论的经籍,多有佚脱之处,自然辩析不通。”于是,他便从头至尾,边读边讲,娓娓不已。大家一听,不觉心生敬服,惊骇不止。
从此,士子们争相前来请教,而澍葊法师也以“通博”的美誉在读书人中树立起一尊丰碑。时间一久,大家还惊异地发现,除了佛教经籍、儒道文献之外,内外方策、九流百家,甚至是说部杂记,澍葊法师无不精通,凡有所问,无不应声解释。有时,那些轻薄少年甚至拿黄书绮语前来请教,澍葊法师也一一穷溯源流,正色应答,人们于是更加钦服不已。
后来,阮文达告归居乡,闻听了澍葊法师的大名,就特地屈尊拜访,相互阐发义理奥意,澍葊法师依然是对答如流,不见丝毫阻碍。阮文达听罢,惊讶慨叹,说他的修证“超然于天人之表,非流俗所能望及项背”。
到了清咸丰初年(公元 1851 年左右), 澍葊法师已然是一位蹒跚老宿了,却依然一如既往,时出应客,为人释疑解难。有时候,他看见少年之徒不务正道,而一味地追逐打闹,嬉戏玩耍,没有节制,不觉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的荒唐,又感伤于日后的灾难,就感叹道:“你们不务正途,嬉戏无度,日后怎么求生?我已经老了,入土为安,不见灾祸,也就罢了;你们却何以存身呢?”大家听他话中藏因,就反复诘问,但澍葊法师却只是摆头,并不回答;问得急了,他也只是黯然神伤,幽思不已。
就在这前后,澍葊法师还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幽居独处,勤修精练,从不懈怠;又以写经自课,抄录无数。尤其是他抄刻的《华严经》等,特别为门徒弟子们所喜欢,往往各自珍藏一部分,以流传后世。
后来,由顽劣凡夫骤然摇身变成为一代法师,似获神助的澍葊法师溘然西归佛国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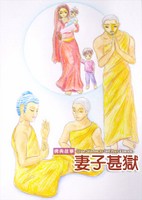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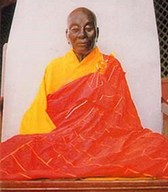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